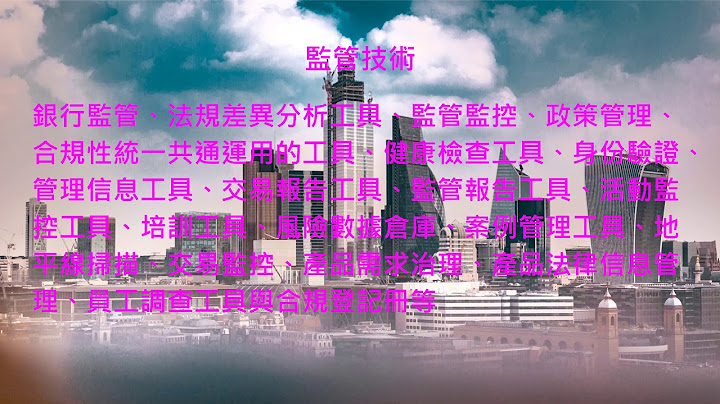在大三专业课上读到这篇名为The Seven Functions of the Hands of Christ: Aspects of Leonardo’s Last Supper (《耶稣双手的七种含义:达芬<最后的晚餐>的多面性》)的文章,属于列奥.施坦伯格较早期的论文,然而该文章之重要性至今仍无可取代;所以凡研达芬奇之画,这篇文章是必读的。且自史蒂芬金的小说《达芬奇的密码》于03年发表,大众纷纷进入一波寻找和讨论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背后神秘信息和预言的热潮中,然今热潮虽退,一个普遍印象已然形成,即达芬奇的画作总是神秘的,背后必有故事。但小说毕竟多是虚构和想象,对《最后的晚餐》的分析为配合其悬疑的情节而过于神秘化。相较而言,施坦伯格的这篇文章修正了小说里关于《最后的晚餐》范阴谋论和缺乏考据的分析。他由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最后的晚餐》的确暗藏玄机,但画家意图之深,画中布局之复杂精妙远比小说的描述高深许多。 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史学者和评论家之一。其学术生涯早期多专注于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研究,并热衷于分析西方艺术中对上帝形象描绘和象征的差异及内涵。对于以往盛行与学术界的关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众多解读,施坦伯格认为因受19世纪支持科学与理性化浪潮及反对宗教狂热的运动的影响而过于简单和世俗化(关于19世纪的艺术评论生态,施坦伯格在这篇论文开头是这么描述的:“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的《哀悼基督》被宣称仅是一次站在解刨学角度的对于人体艺术表达方式的进一步探索;米开朗基罗的《多尼圆画》(Doni Tondo)被认为只是一幅记录家庭户外游乐图景的画作;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不过是一次对耶稣十二门徒在听到耶稣将死的震惊后行为神态的极细致和极差异化的艺术描绘)。因其坚信《最后的晚餐》比传统的解读要复杂的多,这篇论文也就应运而生了;施坦伯格以十页纸近万字详细分析出《最后的晚餐》中可能存在的七条隐秘信息。笔者在国内并未见此文的中文版,本想将整篇翻译过来,但文近十页,相信城市生活的多数难得足够阅读时间和精力,因此就改为一篇对论文核心,即这七条隐秘信息的转述与概括。 根据斯坦博格的理论,整幅画的核心正是端坐聚餐中心(也是画作中心)的耶稣;再精确点,是耶稣的双臂和双手。单就这臂这手就被达芬奇赋予了七种不同作用,每一次作用就将引出一重信息。 第一个作用:画中基督两肩下垂,双手摊开置于桌案,头向一侧略偏,低垂。在斯坦博格看来,这样描画的基督设计的姿态,达芬奇意在用来制造一种将离的悲情,并暗示接踵而来的“耶稣受难记”。因为众所周知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将被钉上十字架。且他也早就预知了自己肉身的死亡即来临,随在晚餐时告诉众门徒这个消息,是他的告别,头略偏向一侧低垂的设计更加剧了这一告别的悲怆,早在斯坦博格之前Walter Peter,著名的英国文学家,就曾评价该画中基督:“他...(在这画中)不是那神坛的主人,只是个与朋友告别的人”。斯坦博格的分析并非凭空想象。在形态学中,高耸有棱角的肩膀无疑象征反抗及强硬的人物性格;而与之相反的耷拉向下的肩膀向来暗示不抵抗顺从的人物特性。据基督教教义,耶稣牺牲肉身于十字架,乃上帝早就定下的安排,意来赎人类的罪。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耶稣必然要接受必须要顺从,那么达芬奇设计这下垂收缩的肩膀的描绘便是暗合耶稣对天命圣父安排的顺从和接受。但这顺从被达芬奇又融入了一些人的情绪,即离别的悲怆。  第二个作用:暗喻三位一体(Trinity),即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指圣父,圣子和圣灵)意为圣父,圣子和圣灵源自同一个本体同一个神,或者说他们是同一神的三个化身。在基督教的图像表达中,三位一体的概念通常以一个等边三角形的符号来表达“三位”同源但不同体的特点。而在《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中,施坦伯格发现,看桌面以上耶稣的上身,他披散下的头发连接肩膀向下经双臂至双手形成成两条线,以其摆在桌面的双手为两个端点连成一条线,这三条线恰好形成了一个几乎等边的三角形,他认为这是达芬奇有意的安排,暗示三位一体,这一至关重要的基督教中心教义。   对比分析以上两种含义,第一重含义展示耶稣离别前的悲怆,此为一种人类的情绪,即人性一面;而第二重含义又暗指三位一体这一严肃的神学理念,即神性一面。人性和神性,二者本相互对立,但确实又共存于耶稣这一人物中。在圣经的描述里,耶稣会为他人的遭遇悲痛,也会对门徒的错误斥责,肉身同常人一样会受伤,钉上十字架后也有一死。那么神性呢?这便不用多说,圣经已有太多记载,比如让死者复活操控自然,最广知的就是耶稣将水变成酒的故事。达芬奇深谙这两重性并巧妙的将二者在画中表现出来,更妙的是在同一位置并同时表现出这两重性。 第三个作用:耶稣的右手指出了出卖他的凶手,周知犹大是出卖耶稣并致其被钉上十字架的始作俑者。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曾对十二门徒说“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中有人要出卖我”,听到此话众人皆惶恐,都问,“主,是我吗?”此时耶稣并未直接指明是谁,只说,“同我蘸手在一个盘子里的人,就是那出卖我的人”。在《最后的晚餐》中,施坦伯格发现画中耶稣的右手,五指伸张形成一个抓取的动作,明显正和犹大的手同时伸向两者中间的一个盘子,这正应了耶稣之前的暗示。  这种理论实则不新,但提出时遭遇多方质疑,质疑的认为这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先入为主,并非达芬奇本意;因为画中13个人餐盘正好13个,每个餐盘都位于一个圣徒面前,很应该是个人的餐盘非公盘,耶稣和犹大的手伸向的盘子正是摆在约翰面前他自己的餐盘,因此质疑的人质疑的是,那么如何耶稣和犹大的手能伸向约翰的餐盘去抓取食物呢?对于这个质疑,施坦伯格的解释很是独特。他并未否定质疑反而接受,认为达芬奇在“同时做两件事”:让这餐盘既是约翰的,又是耶稣和犹大同时蘸手的暗示出卖者的餐盘。施坦伯格提出这个观点并非靠想象,他指出画中的约翰异于画中任何一个门徒,在听到耶稣告知自己将死的消息时没有激烈的肢体动作甚至夸张的表情;再看其手,双手交叠置于桌边,明显远离自己的餐盘。在施坦伯格眼里,约翰安静的面容和姿态是在做耶稣和犹大两手这一出相遇的布景:为了承托表演,没有布景是花哨抢眼的;而其双手的动作则是在为犹大伸向自己的餐盘动作让位。 这里多说一句,上文提到达芬奇“同时做两件事”,施坦伯格认为这是达芬奇创作《最后的晚餐》贯穿始终的心机和深意之一:Ambiguity(中文译作模棱两可,有多重含义和解释),指其同时赋予一个主体多重含义,他们同时成立,又相互独立。但天才如达芬奇哪可满足同时仅做两件事。 第四个作用:耶稣的两手标出圣餐中两大圣物,通过画作或表达或暗示宗教思想和教义的做法在西方宗教画中曾十分普遍,毕竟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普遍识字率之低,对于众多不识一字的普通民众来说宗教画起着沟通教导宗教教义的重要作用,比如马萨乔在其《圣三位一体》的壁画中以十字架上的基督,基督背后矗立的上帝以及两者间的鸽子(鸽子在基督教中象征圣灵)表示三位一体的含义;又比如米开朗基罗在其著名的《创造亚当》中通过描绘上帝手指指向亚当来暗示亚当的原罪是耶稣牺牲和所用人类赎罪的原点这一基督教中心思想。 《最后的晚餐》中可见耶稣右手对准面前的红酒杯,而左手指向面包。二者皆是基督教圣餐中的圣物,红酒象征基督的血,面包则代他的肉身(至今在天主教的弥撒和新教礼拜中仍可见牧师将面包和红酒置于托盘并于众教徒间传递,接到盘子的人食一口面包喝一口红酒表示接受基督为赎人之罪所做的血与肉的牺牲,换言之也就是愿意接受上帝的绝对领导)。  然而这是不是又有视觉上先入为主之嫌,施坦伯格自有其解释和论据。他指出首先耶稣两手各指向基督教两大圣物不可能只是巧合,而且其指向酒杯的右手边正坐着圣约翰(John),圣犹大(Judas) 和圣皮特 (Peter),三人皆是耶稣受难的见证者,而红酒向来是耶稣受难的象征;而其指向面包的左手边紧挨坐着圣徒托马斯(Thomas, 又称Doubting Thomas),圣经记载圣托马斯是圣徒中唯一拒绝相信耶稣死而复生直至其亲眼见其主死后降临面前,并用其一只手伸进耶稣受难后留下的伤口才方信。面包向来象征耶稣肉身,而圣托马斯的故事又无不围绕其对耶稣肉身存在与亡的信与不信。在施坦伯格看来耶稣两手边门徒人物的安排为达芬奇有意为之,旨在支持耶稣双手标指圣物的合理性。  到这你可能会质疑,原先说耶稣右手伸向的是餐盘意在暗示犹大是叛徒,为什么这儿又说他右手指向的是酒杯?这便又牵涉出上文提到的Ambiguity。施坦伯格指出,耶稣右手五指张开,进入其手掌间的只有两物:上一作用里提到的餐盘和现在讨论中的红酒杯,两物紧挨彼此,观者很难分辨耶稣的手到底去向何物,是取酒杯还是向盘中蘸食;施坦伯格相信这种模棱两可(Ambiguity)是达芬奇的有意安排。和分析上一作用时的逻辑相同(餐盘既是约翰的,又是犹大和耶稣共同伸去蘸食的),这里耶稣右手既伸向餐盘,又是要拿取酒杯;也就是说达芬奇既要表现出卖者是犹大,又要展示基督教的圣物。 第五个作用:耶稣两手暗示最后的审判(Last
Judgement),画中耶稣右手手心朝下呈下压状,左手手心向上呈托举状。施坦伯格指出这一手势曾无数次出现在众多描绘最后的审判的宗教画中(最后的审判出自圣经,指世界末日降临,耶稣和其圣父现身对人类进行裁决,信者入天堂获永生不信者降地狱受地狱之火煎烤),画中通常耶稣手心面下象征对不信者的裁判,手心面上代表对信者的褒奖。除了以传统为依据,施坦伯格指出达芬奇在画中也暗埋线索来支持耶稣手势和大审判间的联系。首先,耶稣象征地狱惩罚的右手边门徒间十分拥挤,只从画中左侧墙壁边缘到墙角的距离间就有五个门徒,而耶稣象征天堂永生的右手边门徒排列明显宽敞许多,相对应的距离间只有圣西门,圣达太以及圣马修三人,根据《马太福音》第7章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第六种作用:耶稣左手确定了东面教堂圆顶的位置,《最后的晚餐》是位于米兰恩宠圣母多明我会院内食堂北墙墙面的一副壁画,除食堂外院内还有墓地,僧侣宿舍及教堂。施坦伯格通过对院内建筑以及整体平面图的研究发现如果从画面中心点(在耶稣胸口位置)出发可延伸出一条直达东面教堂的圆顶中心的直线,直线恰好于耶稣象征永生天堂的左手平行,圆顶下方正是神坛即供奉圣母和圣灵的地方。施坦伯格认为教堂圆顶的中心以及神坛的位置是由达芬奇通过其画作中耶稣左手确定的。他的依据在于历史记载达芬奇在创作《最后的晚餐》的同时也参与了教堂和教堂圆顶的改建设计,因此施坦伯格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两点间的联系并非巧合而很可能是达芬奇在教堂改建中利用画中耶稣象征永生的左手来定位建造教堂神圣空间的位置和方向;不仅将画内含义延伸出至画外真实空间,又赋予院内教堂建筑核心点更深刻神圣的宗教含义,此谓一举两得的妙笔。说到这里又将引出达芬奇创作该画的心机和深意之二:In Situ ,即创作同时对画外真实空间的全盘考虑和利用使画作含义不仅停留于画面而是延伸影响至画外空间。因此施坦伯格在文中写到:“如果《最后的晚餐》脱离其所处空间出现在任何复制品中,画作本身将不具任何意义。”这一深意在下一个作用中也将有所体现。  第七个作用:耶稣双手展示神圣力量并延伸至画外空间,施坦伯格认为达芬奇笔下的耶稣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他称之为aura),这里可以理解为神的无上万能(mightiness)亦或是祝福庇佑(blessing),并由耶稣画中双手将这股“力量”视觉上传送进入画作被展示的空间,所以每位观画者将真实感受到这股“力量”,被它击中。这一切描述似乎是施坦伯格的主观感受,但他有足够证据证明这“力量”存在且是达芬奇通过画中布局和透视画法为这无形的“力量”提供了存在空间和外出的通道。  仔细观察耶稣双臂两旁的门徒,门徒与门徒间异常的拥挤几乎不见任何的空隙,但到了耶稣身边,其两旁的门徒,圣约翰和圣托马斯皆身体后倾,在耶稣双臂两边各让出了一片空隙,在施坦伯格看来,是在为耶稣双手传递出的“力量”让步;且从餐桌两边向中心看,餐桌边缘的门徒总还是能身直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越向餐桌中心靠近,也就是越向耶稣靠近的门徒间就越是拥挤堆叠,一些门徒的上身你甚至无法看见,因为被他身边的门徒亦是后仰或是前倾的遮挡住,这一切像是两边的人群被中心的那股力量推开,离中心越近的受其影响越大,倾斜移动的就越多。不仅如此,为了将这种神圣“力量”传播进入画外空间,达芬奇巧妙运用一点透视的画法,因此画中餐厅相对的两面墙,现实中应该相互平行,但画面上却呈现出向外扩展放射状;两面墙又于耶稣展开的双臂平行,施坦伯格指出这给观者视觉上形成两种印象:第一,两面墙壁像是耶稣两边的门徒也被中心的“力量”影响发生了形与质的变化;第二,形成呈向外放射形态的墙壁随耶稣双手指向的方向,向画外无限延伸,也同时是神圣“力量”向画外放射的视觉观感。因此画前身处真实空间的观画者能感受到这股向外延伸出的神圣“力量”。  关于施坦伯格这篇论文的争议一直存在,反对者认为他过于复杂化《最后的晚餐》,强加给画作太多信息,并生套逻辑硬派证据。然而论文作者的反驳是,“对于那些质问‘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暗埋如此多的信息是否可能’的人,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成立,因为对于达芬奇创作此画的动机没有记录也无人知晓。”施坦伯格的意思是:既然没有答案,我的分析经过逻辑推理有论有据,你便不能否认他能成立的可能性。 |

廣告
最新消息
廣告
Populer
廣告

版權 © 2024 zh.ketajaman Inc.